 《苏格拉底的困惑》,〔美〕诺齐克著,郭建玲、程郁华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版,38.00元
《苏格拉底的困惑》,〔美〕诺齐克著,郭建玲、程郁华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版,38.00元
现在搞西学的人还有谁不知道诺齐克呢?人们在谈论罗尔斯的时候几乎总会把他拉过来“陪绑”。然而
先看看诺齐克是否主张自由优先,这其实不难澄清。那种主张自由优先、从自由推导出权利的主张恰恰是《无政府》坚决反对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诺齐克并不认为,自由观念优先于自我所有权并且前者推出了后者”,而是断言:“我们享有的自由的性质及其范围,应该依我们的自我所有权而定。”(《当代政治哲学》,〔加〕威尔・金里卡著,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1月版,第255页)“诺齐克所倡导的自由是基于权利的自由,是一种形式上的程序自由……自由就是有权利去做的选择自由,权利不是自由去做的选择权利。换句话说,我们从诺齐克政治哲学中看到,只能从权利语境中去理解自由,而不能从自由语境中去理解权利。”(《逻辑在先的个人权利:诺齐克的政治哲学》,文长春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93~94页)那种把他归入“自由至上主义”阵营的观点实在欠斟酌。
那么,诺齐克是不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呢?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将个人视为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的终极因素,不承认比个人更具终极地位的“超个人构成物”(superindividual constructs)的存在。《无政府》确实容易给人留下诺齐克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者的印象,因为这本书似乎“把社会化约成抽象的个人,个人具有充分而自足的理性”,并且“认为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在逻辑上只有个人才是第一位的,而社会则是第二位的,个人与社会相比,是逻辑在先的”(同上,第88页)。诺齐克本人从未正面回应过各方面关于该书的评论,不过这本《苏格拉底的困惑》已经足以说明上述印象乃是出于误读。《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一文指出:“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科学理论不可能被化约为人类行动的理论,那么它应该受到谴责(假设我们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正确的话)。但在社会科学领域,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我们目前还缺乏证明某个理论可以被化约的证据……我们似乎不必根据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来决定对那些尚未化约的社会科学宏观理论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态度。和大家一样,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者也必须通过检验正反论据来评价这些理论的正确性。”(《苏格拉底的困惑》,第130页)《看不见的手的解释》一文更直截了当地提到:“经济学用理性代理人的行动对(看不见的手)模式做了典型的解释。但代理人本身的分解理论似乎也可视为一个看不见的手的解释,其中似乎表示某个核心的、统一的定向代理人的模式是被当作更小的、非代理人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来解释的,这也被看作是一个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我的问题是,在某个个体内部,是怎样的去中心化的竞争过程产生了一个(相对一致)的决策者。”(同上,第221~222页)正所谓“?螟之巢蚊睫,?螟之睫又有巢者。视虱如轮,轮中之虱复傅缘焉”――你还能说他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吗?
其实本书序言里有句话可谓泄露天机:“个人选择必须满足什么规范条件与个人应当有权利做出自由选择的范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同上,“序言”第6页)也就是说,权利是自由的前提,而个人选择必须满足的规范条件又是权利的前提。《道德复杂性和道德结构》一文中探讨的“道德观的结构”就为这里所说的“规范条件”提供了一个例子。这种规范性的道德结构未必能说明一个人实际上做出某项道德判断所依据的主观理由,却可以恰当地解释其道德推理的方式,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道德观都在“事实上”符合该结构,或是存在一个所有人的道德观“事实上”共有的结构。如果不知道乔姆斯基在语言学领域开创的“句法结构”理论,恐怕就很难弄明白诺齐克在说什么,“道德结构”正是“句法结构”在伦理学领域的翻版――事实上,这种比“个人”更具有本源地位的结构正是“方法论个人主义”拒绝承认的“超个人构成物”。
毋庸讳言,由于诺齐克对“规范条件”的研究颇为倚重理性选择理论的路径,而后者又往往以个人理性为前提,因此他的不少论述难免予人以主张“个人具有充分而自足的理性”的印象。不过,他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一大贡献却恰恰在于揭示了其内在悖论,亦即本书提到的“纽康柏悖论”――虽然并不是最早提出这个悖论的人,但最先洞察到其深刻意义的人却是他。简言之,诺齐克指出,纽康柏悖论说明了理性选择理论中两条久经考验的原则是相互冲突的:一是期望效用原则(expected-utility principle),一是优势原则(dominance principle)。然而,这两条原则之所以发生冲突,其实是因为纽康柏悖论无非是古老的自由意志与全知上帝之争的博弈论版本。(参见《推理的迷宫:悖论、谜题,及知识的脆弱性》,〔美〕庞德斯通著,李大强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由此大概可以解释,何以诺齐克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会是《恒在:客观世界的结构》(Invariances? the Structure of Objective World)?何以此书竟会广泛涉及数学、量子物理学、演化生物学、经济学、认知科学和神经元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对诺齐克的误解其实是对一种哲学方式的误解,那就是苏格拉底的“诘问法”,正是“这个方法揭示了信念之间的矛盾,从而迫使他人改变某个信念”(《苏格拉底的困惑》,第168页)。诺齐克对“诘问法”的推崇与他对知识论的看法有关。哲学界关于知识的传统定义是“证成了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这一定义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因为受到Gettier问题的冲击而出现了多种修正方案。诺齐克的方案是将知识定义为“追踪真相(理)的真信念”,这一定义旨在面对类似这样的情况:“某个国家的独裁者被杀死了,报上都登出这条消息,但紧接着所有的报纸,乃至还有其他的媒体,都错误地否定了这一报道。所有知道这一否定报道的人全都相信了它,唯独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一报道,因而仍然相信独裁者死了的真相。”此时这个人虽然拥有“证成了的真信念”,但却很难说他具有关于真相的知识,“理由是,假如他听到了第二个否定的报道,他同样也会同所有人一样相信它。”(《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陈嘉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72~73页)――用诺齐克的话说就是他并未“追踪真相(理)”。其实人们对思想、学说的接受也大率如此,严密的思想体系尤其容易使人沉湎于“证成了的真信念”而遗忘了“真相(理)”本身。因此诺齐克无意建构思想体系,甚至无意执著于某一领域或某个课题,而是始终保持思想的“零敲碎打”状态,以“诘问法”贯穿始终。仅仅把他视为一位“政治哲学家”是短视的,仅仅根据诸如《知识分子为何反对资本主义》这样的小品文章来蠡测其深浅就更荒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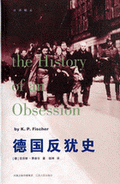 《德国反犹史》,〔德〕费舍尔著,钱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36.00元
《德国反犹史》,〔德〕费舍尔著,钱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36.00元
作者的另一本书《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萧韶工作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版)曾被誉为是一部最好的关于纳粹德国的历史著作,本书之翔实、深刻实亦不遑多让。作者把近代以降德国愈演愈烈的反犹主义归结为民族性格的对立,一方面,“德国人不想把自己看做被赋予固有权益的单个公民,而是把自己想成是一个祖传的血统社会的一分子,里面的每一分子都因种族纽带而紧密相连,共同分享民族的神秘历史传奇和英勇事迹。”另一方面,“作为现代化的传播者,犹太人致力于推进一种长期的、商业的、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念,而这对许多德国人接受他们本质的民族特性产生了威胁。”(第529页)正是长期以来充塞德国上下各阶层的反犹情绪为纳粹的大屠杀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土壤。但他也指出:“整个二战期间,德国民众主体只是怀有歧视性的反犹主义,而不是非要将犹太人斩尽杀绝不可。此种普遍歧视性的排犹主义和引发大屠杀无甚牵连。德国民众没有集体性地决定要发动大屠杀;是他们疯狂的领导人极其保密地犯下了这桩罪行,他们不敢断定是否会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第495页)那种把大屠杀的罪行完全归罪于德国民族性格的极端论点,不仅有悖于历史事实,而且本质上和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即“有些民族因为其种族的遗传天性,从而完全是有罪的”(“引言”第2页)――并无二致。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德国人必须对大屠杀背负的集体责任呢?作者认为,虽然并不意味着每个德国人都有罪,但这一集体责任却是真实存在、不容逃避的――正如一位论者所言,“潜伏的反犹主义与德国民众的冷漠足以让纳粹政权逐渐上扬的导致犯罪的憎恨获得发动大屠杀所需要的自由发展空间。”(第495页)为了弥补过失,德国民族必须永远地放弃以日耳曼为中心的神话,放弃对世界霸主地位的攫取。
 《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38.00元
《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38.00元
本书近年来有数种版本问世,但似乎一直未能引起应有的注意,作者也只是作为钱钟书的父亲而为人所知。实则如欲一睹吾国数千年旧文学的虞渊落照,便不可不读这部成书于1930年、“起王?运以迄胡适、裒然成巨帙”的文学史著作。况且它所论述的并非今日系科分类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志在合《儒林》《文苑》为一体,使人有以推原一代政教升沉陵替之故。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文化立场都是保守的,但迥非“清遗”,而是与晚年章太炎、严复相近,对梁启超“沾沾自喜,时欲与后生相追逐,与之为亡町畦,若忘老之将至”(第395页)的态度颇有微辞,且以章士钊“整饬学风”为“磊落丈夫”之行――想来这种保守主义的论调在当下重审“现代性”问题的文化语境里当不至于覆缶。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土耳其〕帕慕克著,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29.00元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土耳其〕帕慕克著,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29.00元
“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第5页)本书是作者对自己从出生到青年时期走上文学道路之前的成长历程和城市生活的回忆,拜占庭帝国的悠远回响、奥斯曼帝国的迷惘历史、土耳其共和国的威权传统、西方的暧昧影响、家族的式微故事和个人的泥泞心路在书中交织呈现,不胜低回。
《势利:当代美国上流社会解读》,〔美〕艾本斯坦著,晓荣、董欣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版,28.00元
 本书的译名就够“势利”的,原名《Snobbery? The Amer ican
Version》并非专指“上流社会”。虽然不是一个好听的词儿,但“势利”其实在以民主相标榜的美国社会里行使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因为民主“时刻都在发明新的阶级界限,尽管理论上它的本意是反对阶级界限的”(第29页)。不过,在不存在贵族或政府的赞助的情况下,要是再没有势利之徒的附庸,又凭什么维系风雅于不坠呢?
本书的译名就够“势利”的,原名《Snobbery? The Amer ican
Version》并非专指“上流社会”。虽然不是一个好听的词儿,但“势利”其实在以民主相标榜的美国社会里行使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因为民主“时刻都在发明新的阶级界限,尽管理论上它的本意是反对阶级界限的”(第29页)。不过,在不存在贵族或政府的赞助的情况下,要是再没有势利之徒的附庸,又凭什么维系风雅于不坠呢?
